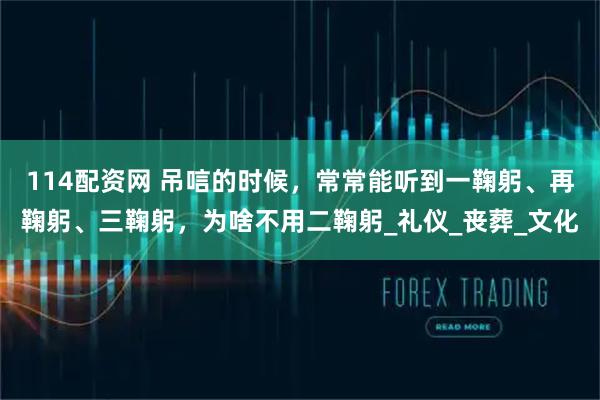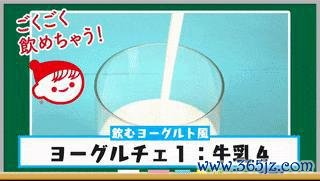如何描绘当下年轻人的生活世界呢?它也许由一点点的欢笑和不同长度的叹息构成广东广州股票配资。
作家伊利亚·爱伦堡说“当今时代就像一辆高速汽车”,你不能大喝:“停下,我要仔细看看你!”你只能“谈谈它的前灯一闪而过的亮光”。
今天的文章,要讲述一个不普通又很普通的故事。一个年轻人,半推半就地进入了非常传统的行业,意外地留了下来,但又不敢停下来。
他知道如何在变动的时代顺流而下,一半听天命,余出的另一半,给自己尽人事。
01.
一个普通年轻人的生活世界
30岁的孙赞每天要抽一包烟。在演出和拍摄的间隙,他都会点上一根烟,接打一个又一个电话。没有电话的时候,他会很安静,想着自己的事情。他同时经营着四家皮影剧场,两家在西安,两家在外地,他总有许多事情要操心。
孙赞有一个听来响当当的身份,叫华县皮影非遗传承人。许多人会因此叫他孙老师,在他听来很别扭。非遗传承人的身份之下,是忙着谋生的普通年轻人。
孙赞出身皮影戏世家,家里人觉得这行出路不多,从不干涉他的职业选择。初入社会时,孙赞从事过两份工作,时间都不长。第一份工作朝九晚五,但工资难以维持生活。他转去加盟了快餐档口,食材主要是鸡肉,没多久遇上了禽流感,换成其他食材,成本又水涨船高,入不敷出。
展开剩余90%“真的是老天爷把我开了”,孙赞说,皮影成了摆在他面前最好的选择。那时孙赞的爷爷带着平均年龄70+的皮影班社,在西安永兴坊驻演,生计不成问题。来看皮影戏的游客很多,其中也不乏年轻人。孙赞决定试一试。
华县皮影戏俗称“五人忙”,表演由五个人分工协作。孙赞的爷爷魏稳柱负责“前声”,是班社的主唱兼指挥,一个人就能唱出生旦净丑。孙赞的嗓音条件不如爷爷得天独厚,改学了“签手”,操纵皮影的角色。
孙赞在爷爷的班社做起了学徒,能跟着师父练手艺不说,还有工资拿。师父对他毫无保留,他也勤琢磨,很快就掌握了基本的操作技能,慢慢也能和班社的其他老人配合演完一出戏。
而后是好几年波澜无惊的上班族生活:表演,领固定的月薪,周而复始。孙赞遗传自爷爷的好胜心开始作祟,他隐隐觉得,“一直待下去就废了”。
2021年,孙赞在西安回民街租了房,开了自己的剧场。由于难以凑齐五人的班社,他不得不效仿很多旅游区的做法,用录音替代主唱和乐手的角色,独留“签手”进行演出。
然而疫情不断反复,有近两年的时间,孙赞从早到晚在店里守一天,只能碰到零星一两个观众。店里只有他一个员工,卖票、沏茶、演出一条龙。没有观众的时候,他就来回把杯子里放凉的水换成热水。
爷爷的班社没能在疫情中撑下去,老人们一起回了老家。而孙赞已经交付了全部身家,只能一天天地坚持着,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。他不喜欢喝酒,心里特别烦的时候会疯狂抽烟。那段时间,是他抽烟抽得最凶的时候。
有一天他等到晚上十点半,才等来了那天的唯一一个观众。观众问他,还演吗?他说没事,你一个人我也给你演。观众有点不好意思,宽慰他说,没事兄弟,我一个人也给你把场子热起来。表演中途,观众果然鼓掌叫好了四五次。
那场皮影戏孙赞是哭着演完的,平复了半天情绪才敢出来谢幕,结果在观众面前又哭了。他从不向任何人诉说心事,但在这样一个陌生人面前,长期积攒的压力像洪水一样倾泻而下。聊完天,观众给了他一个拥抱。
2023年疫情结束,回民街的人一下子多了起来,演出场场爆满。持续在阳康后遗症中的孙赞,用一个半月的时间挣回了近两年的亏损。随之而来的,不是报复性的消费,而是努力工作、攒钱买房、结婚生子。
孙赞变成了不敢停下来的人。就连结婚前两天,他也在忙着剧场经营和宣传拍摄。今年旅游市场没有前两年景气,他担心年底又要赔钱,一有空档就钻研短视频运营,想要在线上劈开一条生路。
早些年他流连网络游戏,而今再也没有休闲娱乐的心气。他在西安待了十几年,还没有去看过兵马俑。
02.
非遗,流动的日常生活史
孙赞不介意用务实的语言谈论皮影,毕竟谋生一直都是皮影从业的首要目的。在集体经济的年代,老一辈皮影人干一天农活的收入是两三毛钱,而演一场皮影戏可以挣到一块钱。
以皮影来谋生,恰恰说明它是日常生活的一部分。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,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了变化,非遗的位置和意义亟需重新阐述。然而非遗从未远离,默默见证了一部流动的日常生活史。
孙赞的爷爷魏稳柱赶上过皮影在大众生活的兴盛,那时候,一听哪个村子有皮影班社演出,十里八乡的村民就会带上小板凳追过去。皮影戏一般集中在秋收后的农闲时节上演,婚丧嫁娶等重要场合也少不了。
孙赞依稀记得,小时候跟着爷爷演出,总是比较快乐。他看不懂戏,只觉得皮影的造型还算有趣,而台下丰盛的席面最诱人,是他童年不可多得的美味。看戏的大人们,则是个顶个的鉴赏专家,戏不好的主唱甚至会被轰下台。
露天电影和电视出现后,皮影戏迅速衰落。魏稳柱陆陆续续去外地接活演出,2015年干脆离开家乡,长期驻扎在西安永兴坊。
皮影在景区延续了生命,却有一种新时代的不得已和不完满。以往长达3小时的剧目,被十几分钟的折子戏取代。相比农村的资深戏迷,景区的观众喜欢看个热闹,《三打白骨精》最受欢迎,一天能连演20场。
孙赞尝试过更换其他的剧目,结果在美团上收到了差评,因为观众就是冲着《三打白骨精》来的。他感觉被困住了,也只能作罢,“演吐了也就那样”。所幸,随着大众对皮影的关注越来越多,他时常能够接到演出交流和跨界合作的机会。
曝光效应,是现今的日常生活中必不可少的存在,老一辈的皮影人也逐渐接受了这件事。传统的皮影戏后台是机密,不允许外人进入。在孙赞的劝说下,爷爷开放了后台给游客参观拍照,也习惯了在镜头下侃侃而谈。
非遗在另一种层面上,回归了日常生活中平易近人的面貌。
03.
没有人,非遗就没有生命
爷爷说,非遗是人不是物质,没有人,非遗就没有生命。孙赞刚入行时,对皮影实在谈不上喜欢。而他第一次体会到皮影的魅力,是被爷爷班社里的老人们打动。
那是在永兴坊的长条状地下室,武戏《刀劈韩天化》正在上演。长号、铙钹、锣鼓的声音形成回响,伴随着老人们“嗨嗨嗨嗨”的呐喊,北宋大将狄青手起刀落,将刺探军情的韩天化斩于马下。
孙赞坦承,一开始只是把皮影戏当作谋生工具,时间长了,也不自觉倾注了自己的情感。这种情感不一定是皮影带来的,而是与皮影相关的人形成的联结。
最早在爷爷的班社做学徒,孙赞就发现班社成员是命运共同体。如果自己顶不上,其他老人就没办法继续待在这里表演。他从这个时候,对皮影的传承产生了微小的使命感。
与他联结最深的人,还是爷爷。他从小由爷爷带大,谈到爷爷为皮影吃过的苦,他就眼眶发红。因为不好意思在人前落泪,只能以出去抽根烟为借口。
孙赞说不清这种复杂的感情是什么,也许是不忍心看着爷爷一辈子的事业付诸东流,也许还有其他的成分。他和爷爷的情感交流不多,但似乎有一种无言的懂得。“男人嘛,不会说很细腻的话。”
皮影戏行业的年轻人不多,孙赞收了6个徒弟,开出不错的薪资,吸引他们留下。他依然感觉很孤独,徒弟们日复一日地上着班,很少把皮影当作事业来经营。他现在的想法是等到暑假过去,做一些经典剧目改编,调剂一下徒弟们的工作。
除了经营上的烦恼,他还有点流量焦虑。他曾经和短视频运营团队合作,被要求扮小丑博眼球,这符合短视频平台的推荐逻辑,却与他真正想传播的内容相悖,于是在合同到期后终止了合作。他为播放数据一筹莫展,只能先自行摸索着。
“传承”二字对他来说太重,他后悔前些年接受媒体采访,说了一些“高大上”的话,给自己造成了额外的压力。而今,他只想坦然地做自己能做的事情。
04.
非遗离我们并不遥远
与孙赞一样,江南布衣旗下设计师女装品牌JNBY,也心系非遗在新时代的延续,在日常生活中的新生。一张皮影,不只是装饰,更是人们用图案表达节气、愿望和情感的生活语言。一场皮影戏,不只是表演,更是一个村庄对故事如何讲述的反复探索。
非遗不是博物馆中死气沉沉的展品,它们的生命始终建立在被使用、被改造、被重新讲述的日常生活中,不会随着时间湮灭。日常生活中也藏着波澜壮阔的历史,正如皮影早就用自己的方式,穿过了几代传承人,走进了我们的今天。
向右更多
自2023年起,JNBY持续在非遗领域深耕,用当代设计语言,重新演绎新与旧。JNBY东方非遗不仅是传统文化,更像是一种看待世界、动手做事的方式。它提醒我们,手的温度、材料的时间感,以及那些未经修饰的、不那么“标准”的美,依然真实而动人。
传统东方的美,在JNBY手下有了呼吸,自然而然地融入当下的生活美学。一件衣裳,便成了非遗的转述载体。当人们观赏它的纹理,抚摸它的质地,嗅闻它的香气,把它附着在皮肤之上,就会意识到,原来非遗离我们并不遥远。
向右更多
图案之美,是非遗之美的重要组成部分。你还记得小时候家里那些“图案”吗?龙、凤、仙鹤、莲花,窗花里的童子、茶缸上的寿星、热水瓶上的玉兔……
那时候我们不懂它们的意义,只觉得它们“该在那儿”。现在想想,那些图案就像小时候的皮影:图像比语言先来,印象早于理解。它们陪你长大,也慢慢消失了。
现在我们想邀请你分享:你小时候最熟悉的图案是什么?它印在哪里?还在你身边吗?有没有哪一个图案,你到现在还没搞懂它讲的是什么?
我们想一起看看,这些图案,是怎么悄悄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的。欢迎在评论区留言,与我们分享你的故事。
与此同时,JNBY发起创作支持平台「100个创作者计划」,以开放的姿态持续连接创作者,推动真实表达。
这里是属于创作者的空间,也是关于日常与想象力的长期实践。在创作上全力发声,在生活上保持清醒。感兴趣可以扫码入群,透过创作,一起发现多样生活的可能性。
采写:布里
监制:荞木
策划:看理想新媒体部
商业合作:bd@vistopia.com.cn
投稿或其他事宜:linl@vistopia.com.cn
非遗并不遥远广东广州股票配资
发布于:北京市粤友钱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